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很少有家乡情结。随着改革开放,居住地日益变化,对父母故乡的依恋感也日渐淡漠。有些人甚至找不到自己的出生地。 。对于出生在农村的人来说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,对家乡的依恋变得陌生。同样的高楼大厦、水泥路,取代了我们祖先建造的土墙、庭院、巷子。田野和村庄正在迅速消失,旧的城市社区格局已不复存在。而人们储存的那些旧记忆,也随着故乡的消失而被抹去。
中国古代早熟的农业文明,决定了远古先民定居田野的农耕生活方式,培养了他们对故土的热爱,熏陶了他们的氏族、宗族、家谱伦理道德。我们想家的根本原因。乡愁的本质是对家乡、故乡的乡愁。家、故乡在人类生命史、人类灵魂史中具有非凡的意义。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来看,建立家园、开垦家乡是人类走出巢穴的步骤。它是原始民居和穴居状态的象征。家是人类躲避风霜雨雪、酷热严寒的地方,土地是人类劳动、耕种、繁衍生息的地方。中国古代的血统和宗法制度也对人们对祖国的热爱起到了强化作用。思乡与亲情的思念、乡愁与亲情往往是相互关联、密不可分的。乡愁的本质是思念亲人,乡愁的本质是亲情。中国人浓厚的宗族血统意识,催生了“父慈子孝、兄弟友弟恭”的伦理道德观念,也有效制约着思乡之人的情感走向。在中国血缘宗法社会的秩序链中,家就是国。国家的雏形是家庭的扩展,引申出来就是国家和世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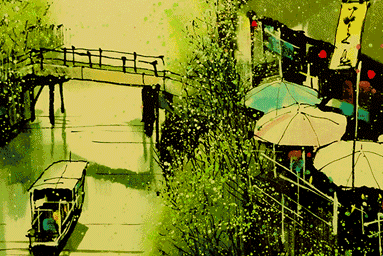
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的代表,也决定着一个地区的品质。对故乡的思念,更深层次上是对文化的仰慕。文化限制人。家乡的水土有独特的自然风光、民俗风情、历史传说、文学艺术,构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传统。在这里长大的人,从小就接触它、渗透它、影响它,逐渐成为一种习惯。 。一旦离开故乡,生活在异乡,那里的人、地都陌生,景象奇特,有很多不适应,游子就会从地域乡愁中滋生出更深层次的文化乡愁。古人有句话:“人面不知去向,桃花依旧笑东风”。古人还有桃花,但我们的家乡早已变了。对家乡的思念不仅是情感层面的寄托,更是灵魂层面的需要。他不仅在寻找身体情感的慰藉,也在寻找生命和灵魂的归宿。李白《客之作》“兰陵有美酒郁金香,玉碗盛琥珀光。 但主人能使客醉,不知身在异国何处。”诗人对故乡、异国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地理。李白一生漂泊,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酗酒、心胸宽广。苏轼《定风博》中的“此心安处,即是故乡”,似乎将我的家乡定位为“心安处”,也就是说,心灵的故乡也可以算是我自己的家乡了。

也许怀旧之情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。每个人的家乡都在衰落。这种感觉更多是出于对城乡现状的不满。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的衰落,没有秩序,不仅仅是家里的老房子倒塌了,记忆中的河里也不再有鱼了。中国现在发展得太快了,我们已经等不及灵魂回归了。南宋诗人刘克庄在《玉楼春》开篇写道:“年年马驰长安城,客舍如家”。这两句话形象地、象征性地表达了在世间无法掌控生活,在动乱中不断奔波、奔波,被巨大的异族势力所支配,无奈疏离家乡。异国他乡的亲近。在古代,情感和生活方式并没有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发生改变。现在的怀旧是,在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下,人类的本源被彻底抛弃。人类与自然、四季没有任何关系,孤独地悬挂在城市的钢筋混凝土中。此时的怀旧,他们想念人的自然属性,想念亲近自然、亲近大江大河的感觉。 “怀旧”的背后,隐藏着多层次的制度和歧视。城市已经无法给他们良好的安定感和安定感。他们有归属感。他们常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。他们看似融入了城市,实则与世隔绝。这是一种非自愿的选择,也是时代潮流所驱动的。我们应该认真反思。如果再不仔细思考,恐怕以后就没有思考的余地了。
“人生就像一场逆境之旅,我也是一个旅行者。”人生艰难的旅途中,你我都是过客,就像各种走走停停的客栈,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过往的悲伤而增添烦恼。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曾说过:“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,但我已经飞过。我的思想是翅膀飞翔的痕迹。生命的意义就是不留下任何东西。只要你有过”经历过,这不是无能,而是一种超然。”希望我们能在“宾馆如家,如家”中过上超然的生活。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
